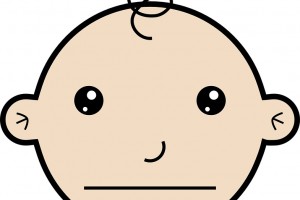每个月都有一次“最后的晚餐”。
“各位乘客请注意,开往衡水的Y501次列车慢慢的开始检票进站了,请各位乘客带好随身物品,抓紧时间上车。”早上7点多,北京西站候车室里,广播声响起,人群开始挪动。
一队队身穿校服的孩子拎着大包小包开始检票进站,有的打着哈欠,有的交头接耳地小声说着什么。
“排好队,排好队,拎好东西,别挤,别挤……”几名老师点完人数开始维持秩序。
北京西站到衡水站,Y501次;衡水站到北京西站,Y502次。
几年以前,谁都不会想到,这趟往返于北京和衡水之间的列车,会成为1300多个“北京孩子”的上学“校车”。
文|柯利刚
监制|张凤云
编辑|十八刀
美编|刘 念
“可怕的”新生
吴霆锋跟同学们随便打了声招呼,便一屁股坐在座位上,叹了口气,发了会儿呆,也不知是早起赶火车累的,还是因为又要离开家人过集体生活而有了小情绪。
坐了一会,他打开书包,书包里装了不少吃的,但他没有拿,而是抽出了一本六年级的课本。在他温习功课之前,我们聊了聊他的衡水求学之旅。
吴霆锋来衡水已经一年多了,除了学校,他对这座城市依然比较陌生,但他对于北京和衡水之间的教育差别有了很多切身感受。
在北京的时候,基本上每天下午3点多就放学了,回家后写完作业,有不少时间可以自己支配,可以看书,可以看电视,“有时候还可以玩游戏。”说到这里,吴霆锋的语调中透着一股兴奋劲。
在衡水,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大多数都在学习,没有太多休息时间,更没有玩的时间。“唯一的放松,就是有时候能和朋友一起去操场上疯跑几圈。”吴霆锋说话语调平缓,说到这里时,透露出明显的低沉和无奈,“我知道总想着玩也不好,但我真的好想玩一玩。”
“刚来的时候,特别想家,特别想回北京。有时候晚上躺着,就是睡不着觉,想着想着,就哭了。”吴霆锋放慢了语速,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接着说,“但是,哭了也没用,因为学校不让带手机,我也不想去老师那里借手机跟爸爸和妈妈说我哭了。就只好自己忍着,忍着忍着,后来慢慢就好了。”
谈到入校之初的那段经历,吴霆锋说起了自己对于“可怕”的理解:真正“可怕的”不是学校的学习,因为基本上已经适应了;也不是自己曾经的哭泣,因为那都已经过去了;真正“可怕的”其实是每年一二年级新生的哭声。
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入学时,有可能也哭,但他们是偷偷哭,是躲着别人哭,是蒙在被子里哭。一二年级的新生,是哇哇大哭,是当着大家的面哭,是不分白天黑夜想哭就哭。
大孩子本来都好好的,但看到或是听到小孩子一哭,有时候立刻就会想到自己。“这种想法不能有,一想起这个,就有可能情不自禁流眼泪。”吴霆锋说这话时,有意别过头去,目光也不再与我对视,“其实大孩子一般不会因为想家哭鼻子,但眼泪有时是会传染的,特别是晚上。”
包子铺旁边的家
所有的这些眼泪,其实都跟老家这个词有关。老家在哪儿?
我以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答案却出乎意料。
“河北省邢台市威县张营乡陆台村”,五年级女生孙梓桐有过几年留守经历,被问及老家,基本上能脱口答出。
“广东省惠来县……”六年级的吴霆锋却只能答到县一级,因为他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老家只回去过一两次,印象不深了。
“爸爸是湖南人……”二年级的李子琳还不明白老家的意义是什么,她自幼就随父母辗转多个城市,对每个地方印象都不深。目前来说,北京是停留最长的一站。
有人曾经留守,有人一直是“候鸟”。
这是一群远离老家的孩子,其中一些人已经不明白老家为何物。老家在哪儿不知道,可家在哪里,总该知道吧。
本来简单的问题,却也得到并不简单的答案。
多数孩子都把“家”的位置指向父母的居住地。诚然,有人才有家,情之所系便是家。
只不过……
有的人,家一直在某一个街道;有的人,家变换过好多个街道;有的人,甚至不知道家在哪个街道。
“我家旁边有个包子铺。”这是李子琳对于家的描述。
“包子铺好多呀,能说得更清楚点儿吗?”
“从包子铺旁边的小胡同进去,一直走,走到小卖部旁边右拐,经过三四个房子就能看见我家了,我家大门是红色的,只是油漆有点旧了。”李子琳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比划,竭尽全力想要描述得更清楚。
其实小孩子不知道,这样的描述,哪怕再清楚,别人也不知道她家住在哪里。大人对于家的定位,是哪个区、哪条街道、哪栋住宅;小孩子对于家的定位,是跟她最有关联的地方,比如卖吃的的地方,包子铺、小卖铺等。
为何需要问家在哪里呢?
因为家在哪儿,决定了你是哪儿的孩子,决定了你可以在哪里参加中、高考。
在衡水人看来,他们是“北京孩子”;在北京人看来,他们是“外地孩子”。
“你感觉自己是哪儿的孩子呢?”
“我也说不清楚自己是哪儿的孩子,”李子琳想了想,带着坚定的语气微笑着说,“我是爸爸和妈妈的孩子呀!”
“那你喜欢包子铺旁边的家吗?”
“喜欢,因为能跟爸爸和妈妈在一起。”李子琳收起微笑接着说,“只可惜,现在每个月只有5天时间能在一起了。”
他们对于衡水的记忆,除了学校就是这座车站。
当头一击的“冀教版”
北京的学生,一周7天,学习5天,休息2天;在衡水读书的“北京孩子”,一个月30天,学习25天,休息5天。
当然,在很多学生看来,这5天还是要打折的。
凌晨5点的北京,夜冰凉、天未亮,初中二年级的孙雨菲睡得正香。
“快起来,快起来,要不然赶不上火车了。”赵红梅打开房门按亮灯,催促孩子起床,“要是每次返校都这么磨蹭,以后就4点多起来。”
这一天,是孙雨菲休假的第5天。
返校的时候,凌晨5点就要起床;离校的时候,到家都晚上11点多了。“5减去2,一个月也就休息3天。”孙雨菲打着哈欠。
“休息3天,还要写作业。我感觉自己根本就没有休息,说是放假,其实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写作业。”孙雨菲指着自己的书包补充道。
休息不足,从来都不是最难的事情。
孙雨菲小学前4年是在北京读的,用的是人教版教材,她学习成绩尚可,从来没觉得课本知识有多难。
冀教版给了她当头一击。
来到新学校,发课本的时候,她有点吃惊,怎么还有个冀教版。等到翻开课本一看,整个人就不好了。
“冀教版数学和英语的难度,简直就是肉眼可见。”孙雨菲说这话时有意加重了语调。
她在心里面告诉自己镇定、镇定、再镇定,一定要预习、预习、再预习。可等到自己真正接触课本内容的时候,之前所有的准备都在瞬间溃不成军。
“预习不明白不算什么,听课不明白才是真打击。”孙雨菲看了看外面还不是很亮的天空,用低沉的语调慢慢地说,“别的同学已经适应冀教版了,我作为插班生,一时之间还不太适应。有时候感觉,一个问题,全班一多半的学生都懂了,就我不懂,打击很大,心理压力更大。有那么一段时间,老师在上面讲,我在下面听,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下来了。”
一开始的时候,考试分数非常辣眼睛。本身功底不错,加之一段时间的勤学苦追,孙雨菲用一学年左右的时间,把学习成绩提升到了班级前列。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适应这种转变,一些从北京转学过来的学生,就一直处于班级垫底的状态。为了让孩子适应衡水的教学节奏,一些家长决定趁早把孩子送到衡水读书。
“狠得下心的家长,一二年级就把孩子送到衡水;狠不下心的家长,三四年级才把孩子送到衡水。”孙雨菲看了一眼旁边的妈妈,平静地说,“再晚送过去,就不太好适应冀教版了。”
每个学生,都是“双城记”的主角。
不及格的德育作业
每个家长都想自己的子女好。
“英才学校的每一次改制,每一步发展,都是在家长的主动要求下推动的。”校长张振友介绍。
学校实行住宿制,是因为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一辈辅导不了作业,在外务工的家长建议学生住校,让老师辅导作业。
学校实行月休制,是因为远在外地(主要是北京)的家长,每周不一定有时间回来看孩子,家长建议月休,一个月能团聚几天。
学校实行接送制,是因为家长来衡水接送孩子,要多花费时间和金钱,因此家长建议在北京完成接送。
接送制的不断改进,也是在家长的建议下完成的。一开始的时候,是分两次列车或多次列车接送。但很快就发现一个新问题:有些家庭,有2个孩子在英才学校上学。分几趟列车接送,家长上午来北京西站接完一个孩子,下午又要来北京西站接另一个孩子;或者是家长刚在北京西站接完一个孩子,又要去北京站接另一个孩子。送孩子的时候也是如此。
怎么办?接送必须一次完成。
于是,Y501、Y502次成为了最终选择。
家长的选择和建议,充分说明他们有心让孩子读书。“现在离开北京,将来考回北京。”家长的想法也充满了正能量。
但想法有时候并不代表行动。
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带够5套以上的内衣和袜子,要做到每天换洗。低年级的小学生,还有专门的生活老师负责孩子们的个人卫生。有时候,放月休假,孩子们洗得干干净净回去。等到月休假结束,孩子们返校的时候,生活老师发现一些学生头没有洗、澡没有洗,甚至衣服也没有换洗。
学校有一个家校联系本,每次月休假都会布置德育作业,这是为了培养亲子感情。德育作业,一般都是做做家务,比如做饭擦地一类;又或是感恩家长,比如为父母洗脚梳头一类。但有的时候,一些孩子的德育作业,空白带回去,又空白带回来。问及原因,一些家长根本就没有翻开,更没有督促孩子完成德育作业。
“课堂作业,家长辅导不了,有很大的可能是学识问题;德育作业,家长没有辅导,更多的可能是认识问题。”小学部的周老师说,“一些家长想法高于行动,想的多、做的少;另一些家长认为学习就是做作业,对其他方面不太重视。”
“孩子就像一棵幼苗,社会、学校、家庭就像阳光、雨露、土壤,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少数家庭的一些孩子,不是缺少这环,就是缺少那环。”张振友顿了一顿,感慨着说,“他们要想成人成才,除了要‘野蛮生长’,还要‘自求多福’。”
算账先生
每一份选择都是精打细算得来的。
去衡水读书,有哪些好,有哪些不好,每一个家庭都打过好多次“算盘”。
对于孙梓桐而言,这笔账比较好算。
老家的学校比较小,大概只有英才学校操场这么大。只有小学,没有初中、高中,而且班级人数也比较少,一个班只有10多人。
老家的教室比较简陋,只有一块黑板,衡水的学校里设备种类很多,有微机室、美术室、图书阅览室等,每个教室里面都有多媒体。
老家的课程只有一些主科,语文、数学是最主要的。这边的课程要丰富一些,每周都有“第二课堂”,有声乐课、器乐课、舞蹈课和美术课等。
“最明显的是厕所不同,老家的厕所是旱厕,能看见好多大便。”说到这里,孙梓桐做出一个要呕吐的动作。
对于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吴霆锋而言,这笔账不太好算。
北京的学校,综合发展强;衡水的学校,成绩提高快。
北京的学校离家近,天天可以见面;衡水的学校离家远,一个月见一次面。
北京的学校学习时间适度,孩子有休息娱乐的时间;衡水的学校学习时间排满,孩子除了学习就还是学习。
在北京上学,不能参加高考;在衡水上学,能参加高考。
……
算来算去,算得很复杂,算得很辛苦,这笔账不容易算清过程,但很容易得出结果。“因为结果只有一个,离开北京才能参加高考。”吴霆锋爸爸无奈地说。
每个家庭总有人要扮演“算账先生”,有些账好算,比如孩子去哪儿上学。在吴霆锋的父母看来,孩子去衡水上学,有利有弊,难说十全十美。
但有些账,不好算,它们看不见、摸不着,往往被忽视。
家庭、情感也是一笔账。
在这些学生当中,一个二年级小姑娘给记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份印象,跟她呆萌的样貌有关,更来自于她有趣的家庭背景。
小姑娘的爷爷奶奶是江西人,外公外婆是四川人,爸爸和妈妈是在北京认识的,一开始做服装批发生意。
后来,北京的服装生意做不下去了,妈妈带着不到一岁的妹妹离开北京去河北固安生活,爸爸远走浙江寻找其他机会,她自己则离开北京去衡水上学。
一家三代人,分散在5个不同的地方。
“我挺想爸爸和妈妈的,但有时候他们说他们更想我。”小姑娘一脸不解地说,“我还是想跟爸爸和妈妈在一起,但他们说这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选择,这些我不是很理解,但哭到最后也只能接受。”
拥挤永远挡不住“回家”的快乐。
《变形记》和莫比乌斯环
Y502次,衡水站到北京西站,用时3小时7分。
这段时间里面,我从1号车厢走到15号车厢,跟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探讨了“现有条件”这个话题。
出乎意料的是,整整一列车的学生,大大小小,对于“现有条件”都比较清楚。在“现有条件”下,他们要么去衡水当候鸟儿童,要么回老家当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这个字眼,他们从不陌生。
除了亲身体验,学校为了激励他们,还组织观看过《变形记》。
在一个由硬卧改成硬座的车厢里,我跟几个初中生深入探讨了《变形记》的观后感。
“观看这部片子吧,效果肯定是有的,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觉得应该努力,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初二学生刘瀚文沉沉地说,“但同时也重温了苦痛,而且是一种感同身受的苦痛。”
“城里人去农村,吃点苦受点罪,那是体验生活;农村人去城里呢,之前啥都没见过、啥都没吃过,‘长了见识’后直接‘怀疑人生’。”王雨桐说。
“就拿节目中的城里孩子王境泽来说吧,现在我们学生之间流行一个词叫‘真香’,意思是说自己的行为打脸自己的话语,或者也可拿来表示剧情极度反转。”陈子瑜轻叹一口气说,“人家参加一期节目,不但出了名,还创造了一个流行词语,但现在还有谁记得跟王境泽交换角色的那个农村小孩呢。”
“叔叔,您知道吗?其实《变形记》还有一个名字叫《平行世界》,我觉得这个名字更好,平行的两个世界,相交的可能少之又少,这可真是残酷物语啊。”赵紫萱低低地说。
走进下一节车厢,基本上全是初中生。一个个小间里,看书的看书,写作业的写作业。我被几个同学的交谈吸引住了,她们正在讨论数学问题。
在闲谈当中,聊到了上一节车厢的《变形记》插曲,这其中,一个女生的思考让我久久难忘。
“在我看来,《变形记》里的农村孩子,就像是站在莫比乌斯环上的行人,就算你一直行走,甚至拼命奔跑,但永远都不可能有终点在前面等着你,你也难以突破自己的维度。”
粗糙与轻松
孩子觉得远,孩子觉得苦,孩子有时候觉得希望渺茫,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家长自发主动把孩子送到衡水读书呢?
这样的一个问题,李玉莲给出了最为坚定的回答。
李玉莲今年38岁,她和丈夫都是河北邢台人。两口子来北京已经10多年了,现在经营一家干果店。
早上6点半一定要出门,晚上9点半以后才收摊回家,一天15个小时以上,这是李玉莲和丈夫一天的工作时间。
“挣钱不多,毛病不少。”李玉莲长长地叹息。
长期站立,夫妻二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静脉曲张;炒干果,油烟不是特别大,但长期近距离接触,两人也都患上了慢性咽喉炎。
“我俩年龄其实不算大,可天天烟熏火燎、风吹日晒,你看他,像不像一个小老头?”站在干果店里,趁着暂时没人的间隙,李玉莲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被冷风吹乱的头发,这也使得头发更显油腻,“你再看看我,像不像一个小老太?”
李玉莲有个远房表弟,前两年娶了媳妇。表弟和弟媳妇是同班同学,只比李玉莲小3岁,他俩大学毕业后都在北京上班。平时两家人各忙各的,一年也见不了一回。
“弟媳妇坐月子的时候,我去看了她一次。街坊邻居,还以为我是她妈妈呢。”李玉莲轻叹一声,“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她们家了。”
父母吃过的苦,不想子女再来一遍。
等到这家店小有积蓄,李玉莲立刻把一双子女接离了老家,送到衡水读书。“老人管不了孩子,一味溺爱;老家的学校也不行,一个班只剩10多人。”
表弟一家人的生活,自己一家人的生活,让李玉莲笃定地相信一个道理:读书能改变命运。
“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容易,房贷压力不小,小孩课外补习也花钱,但他们还是买得起房,我们连买都买不起。最重要的,他们的孩子可以在北京考大学,我们的孩子就不能在北京考大学。”李玉莲坚定地说,“这一切区别都是读书带来的。”
当被问及开始的那个问题时,李玉莲几乎脱口而出:“辛苦,我们是知道的。但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本就应该粗糙一点。娇生惯养,现在怕吃苦,怕受累,将来只会吃更多的苦,受更大的累。”
“现在吃得了学习的苦,将来才能吃口轻松饭。”李玉莲又说起了她远房表弟的相关经历,她讲述得如此清晰,好像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她自己身上一样。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学生名字皆为化名。)
农民日报脉动工作室出品
作者简介:
柯利刚
走过千山万水,
最爱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