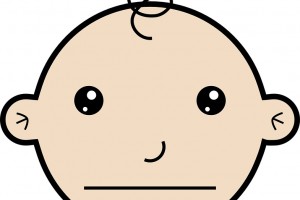邵永义
我是个底层文明工作者,前不久有幸得到一次去北京大学训练的时机,能走进我国新文明的发源地,尽管仅仅七天的游学,我也满怀忠诚,备加爱惜。
刚下飞机,脚上那双毛皮鞋因爱热而根柢开裂,从机场出口到上车,从下车走进北大住宿点,每走一步都有老化了的橡胶底成碎渣一块块掉落,严重影响了首都的环境卫生,但我佯装镇定。晚上联系到浙江的小师妹,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的芳芳,我忙着买鞋,她忙着请我吃饭,坐在一家超市的用餐厅,我告知她自己是从四川走到北京的,她不信,我把脚从饭桌下抬起来,两只鞋底都快掉光了,看得见袜子。她大叫了一声,惹得餐厅里吃饭的人都把目光投向咱们。饭后买了双新皮鞋穿上,我用塑料袋把那双没有根柢的毛皮鞋装好。离别小师妹我打的回住地,下车后瞅到一个垃圾箱,我把那双鞋塞进了“可回收”的口儿,做贼似的敏捷离去。
第三天从食堂吃午饭出来,在很多的海报启事中,赫然闪出一条红布标语:丹麦前期前期奠基人艺术特征赏析。
我提早找到了开讲座的梯形教室,在前几排里边靠窗的当地找个方位坐下来。年青的学生连续走进了教室,他们阳光灿烂,或花枝招展,也没人太介意我这个老学生。
讲座开端了,昨日给咱们上课的李教授非常儒雅地上了台,作了一段开场白,我好像找到了自傲,还拿出了笔记本。李教授用英语请出今日的主讲教授,一位身段魁伟而不失绅士风度的洋教授。洋教授在同学们火热的掌声中走上了陈述席,他双手扶在陈述台上,嘴里快速地蹦出一长串的英语。我开端不安,继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冲击:想想,整个学术陈述会都用英语沟通,除了一句“罗曼蒂克”,我简直没听懂一个单词。学生们听到精彩处都宣布会意的浅笑,而我不知所言,当学生们拍手,我也跟着拍手——当然,是瞎拍手。
教室济济一堂,我想溜号了,但方位太靠前,必定是众目睽睽下的逃跑。我用浅笑和故作深重的允许来粉饰自己的为难。总算,洋教授开端播映一个个是非电影片段,缓解了我的压力。其间一女孩受绞刑前,她母亲撕心揪肺地冲上去和她拥抱,被法警驱退。女孩面向她母亲和围观的乡民,唱了一段歌曲,音乐从衰婉转向沉着……我不由得在音乐的结尾中兴起掌来,接着是教室里暴雨般的掌声。
观赏798文创园出来,我的手机掉在出租车上了,当天有在北京的乐山词赋家、诗人梅隆雪川约我吃晚饭,上午电话中说他还请了几位在京的四川文明人,下午发地址给我。我没了手机,也记不起他的手机号,到晚上还想着他电话打不通的着急表情。这个践约的结果是:当晚雪川和几位四川老乡在火锅店里比及八点过才开端焚烧,我后来用了几斤峨眉茶叶向他们赔礼。
一高中同学在北京农业大学做教授,约好晚上八点在北大老校门“燕京大学”牌子下见。他电话说打车过来,好喝酒。我很早就赶到“燕京大学”老门,成心把自己亮在台阶上。我和他高中毕业后就各自东西,30多年未见面,很怕对面曩昔不相识。我机警地目视街上。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面前,一中年男人还没下车就大声叫我的姓名,我不敢认这个黑脸膛、头发篷乱、穿赤色冲锋衣的男人,仍傻傻地问:“你真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