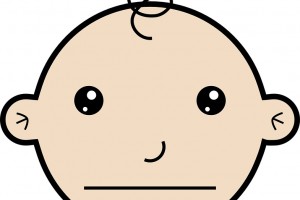让我们通过分别分析每一个参数,来重新审视德雷克方程。
R,也就是银河系每年产生新恒星的速率,确实大约为1——天文学家对这一点非常确定。事实上,天文学家最近发现,目前可能拥有智慧生命的恒星,在几十亿年前的形成速率更快。所以R=3的取值更加切合实际。然而,天文学家和生物学家对方程中接下来的参数就没有这么确定了。
第二个变量是fp,也就是具有行星系统的那一部分恒星的数量。最近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年轻恒星周围都环绕着行星形成盘,而且自1995年以来,天文学家观测到了几十个周围环绕着行星的类似太阳的恒星。这些发现证实了天文学家一直以来的猜想:行星系统对恒星来说是普遍存在的。
原行星形成带通常可以通过红外观测检测到,很多照片也拍到了,例如哈勃空间望远镜拍摄的猎户座星云。猎户座星云是我们银河系中最多产的恒星形成区域之一。亚毫米波观测经常会显示,在许多年老的恒星周围环绕着稀薄的尘埃盘,例如德雷克的第一个观测目标天苑四。这些行星盘中很多都是甜甜圈状的。根据许多理论家的说法,中间的空洞只能通过行星盘内侧的行星汇聚气体和尘埃的加积作用来清理干净。另外,一些行星盘(包括天苑四)的扭曲直接显示,在外侧区域有一颗行星在运转。
至于实际检测到的行星,截至2013年6月,太阳系外行星搜寻发现,类似太阳的恒星中,大约12%在5个天文距离(相当于木星与太阳的距离)之内拥有一颗巨大的行星。表面上看,这或许暗示12%的恒星具有行星系统,因此fp的值为0.12。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目前的搜寻技术只能检测到大型行星,尤其是那些在小而快的轨道上运转的。
像太阳系中的行星这样的目前还无法被检测到,再过几年应该就可以观测到了。类日恒星拥有某种行星的比例很可能高于12%,在目前看来,从20%到100%都是合理的猜测。查尔斯·莱恩威弗和丹尼尔·格雷瑟在2013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深入探究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些观测结果让我们对fp有哪些最新的认识呢?虽然目前我们没有最终值,但有两点很明确,fp的值很大,并且在德雷克方程中不是一个瓶颈。
德雷克方程中的另一个参数ne就没有这样确定的信息了。这个因子代表典型的类太阳系中具有适宜生命起源环境的星球的平均数量(e代表“类似地球的”)。在1992年出版的著作《外星生命在哪里?》中,德雷克回忆道,在绿畔会议上,参会者推断ne的取值为1至5。换句话说,每个行星系统都被认为应当具有至少一颗类地行星(定义为可能存在液态水),可能拥有3颗、4颗或者5颗这样的星球也不是一件难事。
这一乐观看法基于太阳系是一种典型系统的假设。今天,火星和木星的卫星木卫二被看作具有早期生命的可能地点,根据德雷克公式的定义,太阳系拥有3颗类地星球。然而,过去几年中发现的太阳系外的行星给我们上了一课,让我们意识到,像太阳系这样的拥有许多漂亮的有环形稳定轨道的行星和卫星的系统可能是一个例外,而不是一种常态。就我们所知,拥有长期稳定的轨道和气候的类地行星可能非常稀少。
目前科学界对fl取值的关心跟过去相比已经非常少了,这一因子代表适宜生命居住的行星中真实存在生命的比例。
构成生命的基本分子元件——复杂的有机化合物甚至氨基酸——在宇宙中含量丰富。在陨石、彗星、星际气体和尘埃中都发现了它们的存在。星际空间中的氨基酸含量就比地球生物圈中的含量高很多。虽然碳氢化合物和氨基酸并不是具有活性的生命形式,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在星球之间的暗云中,很多生命前演化正在进行。
最重要的是,近期的发现显示,虽然39亿年前年轻的地球上发生了许多毁灭性的、足以使海洋蒸发的事件,但是微生物紧接着就出现了(从地质学的角度上讲)。有清晰的证据显示,35亿年前细菌就出现了,另一些受到更多争议的证据则表明这些细菌在37亿甚至是38.5亿年前就出现了。显然,如果条件合适,生命的起源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的直观过程——至少,在整个星球都是实验室并且这个实验能够直接进行几百万年的时候是如此。
如果这一过程稀有且艰难,那么它就不会在这个星球一形成就发生,因为它需要足够多的时间试错。生物学家目前在讨论,生命的起源是不是分别发生了很多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今天的所有生命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但是其他独立的生物进化链也可能很早就形成并且被淘汰了。如果生命确实可以在任何地方产生,那么可以假定fl=1。
这就剩下了3个未知因素。进化产生智慧生命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有多大的把握认为,至少有一些外星智慧生命会向宇宙空间发射我们大家可以检测到的无线电信号或者其他信号(fc)?能够发射无线电信号的文明的平均寿命(L)又是多长?德雷克方程里的这些生物学和社会学因素受到的科学争论和它们本身的不确定性比天文学因素更多。
生物学家指出,设想其他行星上的进化过程会产生我们熟知的这种智慧生命是一种非常天真的行为。已故的哈佛大学古生物学家史蒂芬·杰·古尔德在他的畅销书《精彩的生命》中断言,“我们也可以存在,或许得感谢好运气。智人是一种存在,但不是一种趋势”。进化无法预测,没有方向,混乱无序。古尔德多次指出,如果我们大家可以把地球上的生物进化过程倒带,再重新开始,人类就不可能再次出现在图景中。我们是一系列侥幸成功和偶然事件的结果。
其他人反驳说,我们寻找的不是人类。没有人指望在其他星球上找到人类(不管是小绿人还是其他)。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本质是,是不是会有物种进化到可以产生以抽象思维为基础的智慧,可以存储和操作信息,并发展出足够大和复杂的社会以发展科学的程度。对乐观者来说,这看上去只是智慧程度的差异,并不是智慧生命种类上的差异。地球上多样化的动物物种,从猿猴到章鱼,就独立进化出了各种层次的智慧。
但是古尔德指出,进化并没有一个总体的模式,没有喜好的方向。如果近期进化出的一种动物比之前的那些体型更大并且更聪明,这很可能仅仅是一种侥幸。人类层面的规划和技术可能更是如此。
对一些生物学家和SETI的支持者来说,“适者生存”这句话暗示更高等的智慧一定会提高一个物种在自然选择中存活和扩张的概率。但是已经从哈佛大学退休的著名生物学家欧内斯特·迈尔指出,很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对于智慧生命的产生过于乐观了。“跟生物学家相比,物理学家更倾向于用宿命论的方式思考。”他在1996年5月的《行星报告》中写道,“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果生命在一个地方产生,在一定时候就一定会发展出智慧生命。”生物学家则认为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可能的。
奇怪的是,无论是乐观论者还是悲观论者,他们的观点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关键的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星球,技术的产生经过了40亿年。像迈尔这样的悲观论者(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现实主义者)把这一点看作在一个给定的进化中不太可能产生智慧生命的证据。对乐观论者来说,这反而增强了他们对地外文明存在的信念。
这种差异产生于专家不同的学术背景。对生物学家来说,40亿年中只发生一次的事情是极度罕见的。天文学家的视角则更为开阔,在他们看来,在行星的生命周期中能够发生一次的事情,对所有行星来说都是合理的。
乐观主义者指出,一些估算表明,在地球被膨胀的太阳吞噬之前,它还有12亿年的寿命。这比第一批简单生物从海洋爬上陆地到今天为止的时间要长出好几倍。他们因此认为,如果智慧生物的产生困难并且罕见,它就不会在地球上相对早期的阶段产生。考虑到人类在地球生命的漫长纪元里出现得很早,看上去在今后的地质年代里很可能会出现若干种完全不同的智慧生命(它们可能会找到我们的化石)。这一论点与由年轻的地球快速出现微生物引出的观点相吻合。
悲观论者回应说,我们并不知道地球上的温和环境还能维持多久。地球上看起来很稳定的环境或许是一系列侥幸的结果,在地质年代的层面上讲,可能随时都会结束。如果这样想,人类出现的时间在整个可利用的时间跨度上其实是很晚的。这或许表明智慧生物的产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与流行的观点相左,智慧生物只产生了一次这一事实,并不能告诉我们它多久能发生一次。原因很简单,人类的出现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只是自我选定的特例。即使智慧生命的产生几乎不可能到仅仅在宇宙一个偏远的角落里发生了一次,我们也必然会在那个角落里观察这个事件,因为我们就是这个事件。
更加奇特的是,两方阵营都接受所谓的哥白尼原理。该原理主张,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位置偏好性。像迈尔这样的怀疑论者说,认为类似人类这样的智慧生物在宇宙中不断产生,是以人类为中心衡量宇宙。像德雷克这样的信仰者则不愿意接受我们的独特性,因为这会把我们置于一个非常不符合哥白尼原理的基础上。
SETI研究所宇宙生命研究中心的主席克里斯托弗· 切巴总结说:“这是一场关于进化的偶然性和趋同性之间相对重要性的争论。”换句话说,进化趋势中有多少是随机的侥幸事件,有多少是重复驶向同一个方向的。“有没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聚焦和量化这一论点的数据?” 切巴继续说,“答案看起来很响亮,是!我们不需要猜测这样一些问题,而是可以开始使用已被充分理解、可以量化的工具来量化评估其中一些问题。”SETI研究所正在组织科研人员对这一问题进行攻关。
然而截至目前,fi是德雷克方程里最具争议性的一个因子。一些科学家认为它几乎一定接近于0,其他人则确信它接近于1,看上去没有中间立场。
即使智慧生命是进化的可能结果,fi或许也比1小很多,这一推论基于最近关于太阳系和行星气候稳定性的深入研究。一颗行星开始时适于生命的生存,并不代表它会一直如此。
麻省理工学院的弗雷德·瑞希欧和艾瑞克·福特等人的计算机模拟显示,如果一个行星系统里同时存在两颗(甚至更多)木星这样的巨型星球,像地球这样的行星是无法在它们的重力拔河比赛中存活的。它或者会被抛出这个系统,或者会倾斜到被中间的恒星吞噬。
与此相反,如果系统里没有一点巨型行星,同样可能会对可以孕育生命的行星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的乔治· 威瑟里尔的计算机模拟表明,木星起到了太阳系中重力吸尘器的作用,有效地减少了会游荡到地球轨道上的危险彗星的数量。威瑟里尔说,假如没有木星,目前彗星撞击地球的概率将会高出1000倍,这中间还包括每10万年就会发生一次的真正灾难性的碰撞(像6500万年前让恐龙灭绝的那一次一样)。这一定会给从简单生命形式到高级智慧生物的缓慢进化过程制造大麻烦。
另外,法国经度管理局的雅克·拉斯卡和菲利普·罗本泰进行的动力学研究表明,岩质的类地行星显示出了混乱的轨道倾斜改变,这可以导致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幸运的是,地球的这种无序倾向被跟月球之间的潮汐作用减弱了。假如没有一个大型卫星,地球或许会跟火星一样,具有高达20°到60°不等的轴倾角变化。这将会导致季节模式的极端变化。根据一份行星形成的分析报告,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只有1/12的机会拥有一个由大型卫星稳定住的温和轴倾角。从另一方面讲,一颗没有月球的地球或许会保持自己原有的快速旋转,这也可以稳定住旋转轴。每个人都可以猜测轴的摇摆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生命的进化和智慧生命产生的机会。生物学家说,变化和压力其实
可以促进新的、全能的、可以适应环境的物种产生。例如,哈佛大学的保罗·霍夫曼及其3位同事在1998年提出,7.6亿年前到5.5亿年前在全球发生了一系列冰川时期,这场危机在同期或者稍后的时间内创造了非凡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地球地质记载下来的灾难性大灭绝总是伴随着具有活力的恢复,最终产生比之前更多的物种。无论大灭绝发生的范围多大,此后的彻底恢复似乎总是需要1000万年。人类在一次不寻常的冰川期出现,这有时候被当作一个压力驱动进化导致适应性和智慧生命产生的例子。因此,一个拥有不稳定旋转轴的行星很可能会加速进化过程。
但是,如果行星危机太极端或者太频繁,就会杀死一切,或者将生命形式镇压到最低的层次。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的存在,似乎是一系列天文巧合的结果,这在1961年是没有被设想过的。
这些巧合在彼得·沃德和唐纳德·布朗李的著作《珍稀地球》一书中得到了详尽的讨论。沃德和布朗李提出,产生一个适宜生命生存的星球,并且在孕育高级生物的几十亿年间保持对生命友好的环境,是一件极度罕见的事。SETI研究所的塞思·肖斯塔克在一篇反驳文章中说,他们的一些观点夸大了。生命一旦建立起来,就可能有足够的适应性在非地球类的条件下繁荣起来,因此不需要一个星球具有狭义的类似地球的历史。
沃德和布朗李的同事吉列尔莫·刚萨雷斯倡导的观点是,在银河系中只有一个狭窄的“宜居环”,在这里,条件适宜,生命能够存在。靠近银河系的中心,生存条件可能过于恶劣,离中心更远的地方则没有足够的重元素来产生行星。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个想法过于粗略,也严重夸大。事实上,重元素广泛分布于一个星系的星盘中(这一点的证据是显而易见的:由碳和硅形成的灰暗的尘埃云充溢着大多数星盘的大多数区域),很多具有行星的恒星系重元素分布范围相对宽泛。
来自银河系中央的危险射线会被行星周围的大气层阻挡,这也是我们把X 射线望远镜和伽马射线望远镜送上轨道的原因。大卫·达令在他的著作《无处不在的生命》中指出,刚萨雷斯是从自己的宗教信仰出发提出了新天体生物学。他在其他著作中表示,上帝为一种智慧生命创造了一种世界,而刚萨雷斯的天文学观点应该放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