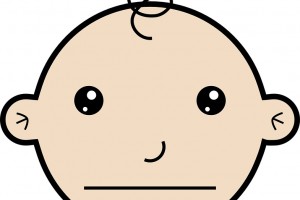文|肖复兴
最近最近一段时间,和外界的联系,完全靠微信。前天,突然收到一位老街坊的微信,问我:小鱼前些天走了,你知道吗?我大吃一惊,小鱼只比我大两岁,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赶紧问他:是得了新冠肺炎吗?回答说不是,具体什么病,他也不清楚。
那天,我坐在屋里,望着窗外空荡荡的街道,眼前总是晃动着小鱼的身影。
那时候,我和大院的孩子们都管小鱼叫“指甲草”。这个外号,是我给她取的。指甲草,学名叫凤仙花。凤仙花属草本,很好活,属于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花种。只要把种子撒在墙角,哪怕是撒在小罐子里,到了夏天都能开花。凤仙花有粉红和大红两种颜色。女孩子爱大红色的,她们把花瓣碾碎,用它来染指甲,红嫣嫣的,很好看。我一直觉得粉色的更好看,大红的太艳。那时,我嘲笑那些用大红色的凤仙花把嘴唇和指甲涂抹得猩红的小姑娘,说她们涂得像吃了死耗子似的。
放暑假,大院里的孩子们常会玩一种游戏:表演节目。有孩子把家里的床单拿出来,两头分别拴在两株丁香树上,花床单垂挂下来,就是演出舞台前的幕布。在幕后,比我高几年级的大姐姐们要用凤仙花给每个人涂指甲,还要涂红嘴唇,男孩子也不例外。好像只有涂上了红指甲和红嘴唇,才有资格从床单后面走出来演出,才像是正式的演员。少年时代的戏剧情结,让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跃跃欲试,心里充满想象和憧憬。
我特别不喜欢涂这个红嘴唇,但是,没办法,因为我特别想钻出床单来演节目,只好每次都让小姐姐给我抹这个红嘴唇。凤仙花抹过嘴唇的那一瞬间,花香挺好闻的。其实,凤仙花并没什么香味,是小姐姐手上搽的雪花膏的味儿。
这个小姐姐,是我们演节目的头儿。她就是小鱼。
我既有点讨厌她,又有点喜欢她。小孩子的心思就是这样复杂。讨厌她,是因为每次演出她都像大拿,什么事情都管,总嫌这个孩子唱得不够好,那个孩子跳得不够高,好像她是个老师。大院里的演出,又不是舞台上正式的演出,哪有那么标准?不就是一个玩吗?喜欢她,是她长得好看,我们大院里的老奶奶说她长得像年画里走下来的美人儿。还有,给我抹红嘴唇的时候,她手上那种凤仙花的香味儿。
现在想,那时候给她取外号,为啥不叫“凤仙花”,偏偏叫“指甲草”呢?她应该是一朵花,不是一棵草。不过,我不是诚心要把她贬低为一棵草的。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指甲草的学名叫凤仙花。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读初一。有位拍电影的导演到她的学校里挑小演员,相中了她,让她跳了一段舞,又唱了一首歌,当场就定下了,让她回家跟家长商量一下,家长同意,就带上她到剧组报到。学校老师很高兴,这是给学校扬名的好事。她自己当然更高兴,她本来就喜欢唱歌跳舞,喜欢演节目,马上就可以当一名小演员了,这不是跟天上掉下馅饼一样!
没想到,她爸爸和妈妈死活都不同意。她妈妈是医院里的护士,爸爸是个工厂技术员,他们意见一致,都觉得当演员不是正经的事。当学生,就得把学习成绩弄好,将来上大学,才是正路子。他们都是那种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老派人。她爸爸就是大学毕业,她妈妈就是看中了爸爸是个大学生才嫁给他的。
正如白天不懂夜晚的黑,大人们很难懂得小孩子的心思。爸爸和妈妈的不同意,竟然让小鱼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当时包括小鱼在内的我们大院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说起小鱼,街坊们都会叹口气说:唉!老天真是不长眼呀!小鱼并没有如爸爸和妈妈期待的一样考上大学,实际上,自从初一演员梦破灭之后,小鱼的学习成绩就开始下滑。高中毕业之后,小鱼没有考上大学,先在一所小学当音乐老师,后来又跳槽到文化馆工作,都和表演沾点边。但她并不快活,她的不快活,又波及她的爸爸和妈妈。因为无论爸爸和妈妈怎么催,怎么帮助她找对象,她都没有心思。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那年,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当老师,她还不到三十岁,风韵不减当年。说老实话,如果不是我在北大荒有对象,真的有心想找她。可是,我知道,她看不上我。她能看得上谁呢?
后来,她爸爸单位分了楼房,一家人搬走了。我很少再见到她。后来,听说她得了病,人消瘦了很多,甚至脱了形,再也没有当年漂亮的模样了。当时,人们都不大懂,她自己也是乱吃药,现在想想,她得的应该是抑郁症。
她的爸爸和妈妈过世得早。老街坊们都说,如果不是因为她,不会这么早就过世的。但是,我说,如果不是因为爸爸和妈妈当年拦腰斩断了她的梦想,她不会有这样的命运。
不过,命运是什么呢?谁也说不清。街坊们常说命运就是老天爷早就安排好的事。一个人的命运,对比浩瀚苍天,真的是微不足道。
如今,她走了。也许,是一种解脱吧。我的心里,却总不是滋味。她本是一朵花,最终成了一棵草。怨谁呢?或者,作为我们普通人,本来都属于一棵草,就不应该做一朵花的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