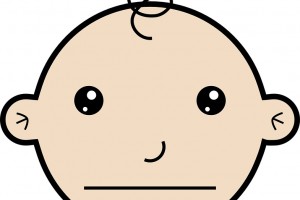文丨梁衡
钟声一响,已进不惑之年;爆仗声中,芳华已成昨日。不知是谁发明晰“年”这个怪东西,它像一把刀,直把咱们的生命,就这样寸寸地剁去。可是人们如同还欢迎这种切剁,还张灯结彩地相庆,还美酒盈杯地相贺。我却暗暗地咒骂:“你这个叫我百般无奈的家伙!”
你在我生命的直尺上留下怎样的印记呢?
有许多当地是浅浅的一痕,乃至今日想来都忆不起是怎样划下的。当小学生时苦等着下课的铃声,盼着星期六的到来,盼着一个学年快快地逝去。当大学生时,正赶上“文 革”的时代,整日乱糟糟地聚会,不行思议地激动,慷慨激昂地奋斗,最终又都将这些一把抹去。发配边远当地,白日冷对大漠的孤烟,夜里眺望西天的寒星。这许多年月就这样 在我心中被烦恼地推开,被急切切地赶走了。年,是年年过的,可是除却划了浅浅的表明时刻的一痕,便再没什么。
但在有的当地,却是重重地一笔,一道深深的印记。当我学会用笔和墨作业,知道向常识的长河里汲取乳汁时,也就懂得了把时刻紧紧地攥在手里。静静的阅读室里,忽然 下班的铃声响了,我百般无奈地合上书,昂首瞪一眼管理员。本是被拦蓄了一上午的时刻,就让她这么悄悄一点,闸口大开,时刻的绿波便洞然泻去,而我立时也成了一条被困在干 滩上的鱼。当我和挚友灯下畅谈时,司马迁的文,陶渊明的诗,还有伽利略的试验,一同被桌上“滴答”的钟声拌和成一首美丽的旋律,咱们沉醉,咱们盼夜长,最好长得没有底。而当我一人伏案疾书时,我就用尖利的笔尖,将一日、何时撕成分秒,再将这分分秒秒点瓜种豆般地填到稿纸格里。我拖着时刻之车的轮,求它慢一点,不要这样急。可是年,还 是要过的。记住我榜首本书出书时,正赶上一年初的岁末,我悄然对着墙上的日历,久久地像望着山路上远去的情人,望着她那飘逝的裙裾。但她也没有负我,留下了手中这本还 散着墨香的厚礼。这个年就这样藕断丝连地送去了,生命直尺上用汗水和墨重重地划下了一笔。
想来孔子把四十作为“不惑”之年也真有他的道理。人生到此,正如行路爬上了山巅,登高一望,回忆曩昔,我顿理解,本来奸刁的自然是悄悄地用一个个的年来换咱们一 程程的生命的。有那聪明的哲人,会做这个生意。牛顿用他生命的第二十三个年初换了一个“万有引力”,而哥白尼垂危床头,还挣扎着用生命的最终一年换了 一个簇新的日心说系统。时刻不行留,但能换得成一件事,理解一个理,却永不会失掉。而我曩昔多傻,做了多少赔钱的,不,赔生命的买卖啊。假若把曩昔那些乱糟糟的日子压成一块海綿,浸在知 识的长河里能饱吸多少汁液,倘若把那寒夜的苦寂转为活跃的思索,又能悟出多少道理。时刻这个严寒却又公正的家伙,你无情,他就无意;可你有求,他就给予。人生本来就这 样被年、月、时,一尺、一寸地度量着,人生又像一支蜡烛,每时都在做着物与光的买卖。可是都有一部分蜡变成光热,另一部分变成泪滴,年,是年年要过的,爆仗是岁岁要响的,美酒是每 回都要斟满的,不过,有的人在傻乎乎地随人家春节,有的却微笑着,窃喜自己用“年”换来的成功。
这么想来,我真清楚了,真不不惑了,我不应咒骂那年,倒懊悔自己的曩昔。人,假设三十或二十就能不惑呢?生命又该焕宣布怎样的价值?
作者:梁衡,1968年结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闻名散文家、学者、新闻理论家、政论家和科普作家。曾任《内蒙古日报》《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书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修改。